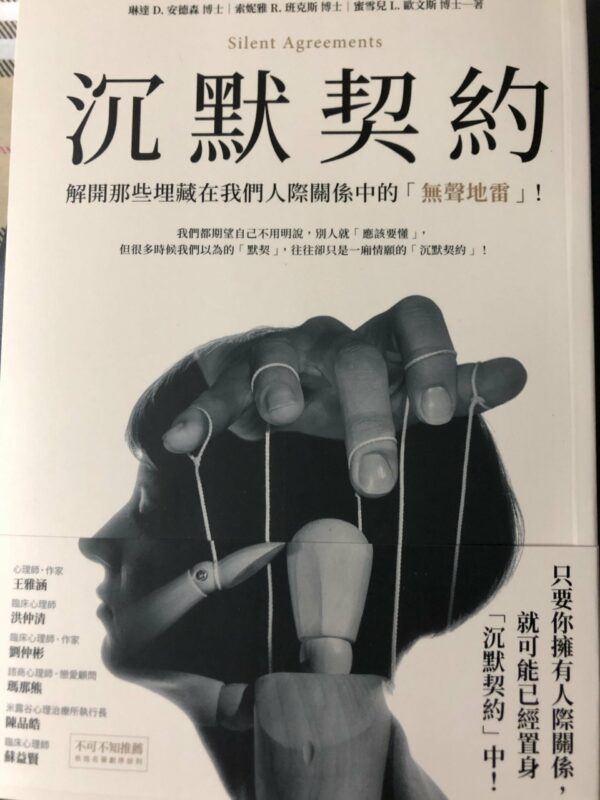開始夢到麻糬是最近的事情。
期末家聚之後,麻糬的形象就一直在我腦袋中揮之不去,像是穿著草裙,搖晃著渾圓的身體,嘴裡一邊還唱著原住民歌曲那種麻糬。
說起來我並不討厭麻糬這種食物,但是也並不是十分喜歡,世界上就是存在著這一種介於喜歡與不喜歡之間,或許可以稱做穠纖合度式的感覺,但若硬要做一個區分的話,我想他比較接近討厭的那一邊,就如同我們的肌膚是弱酸性的一樣。
「小花,你要吃嗎?那我就不客氣摟。」學伴用三隻指頭的指腹像是夾娃娃機的爪子似的抓起麻糬的腹部,一口送進嘴裡,唇邊沾黏著些許的白色粉末與紅豆餡,她向學妹借了一張衛生紙,用一種威脅紅豆分子的姿勢拭去唇邊的殘餘物。
「是怎樣的夢境內容呢?」黑狗兄問,右手來回地控制休旅車的方向盤,左手兩指間夾了一根香菸,手的三分之二露在窗外,任憑風幫他抽他的香菸,煙如同一條白色的水蛇,向後車燈爬去。我曾經也懷疑,只有三隻手指的黑狗兄是如何控制方向盤的呢?但我顯然是多慮了,連手指都不需要用到,只需要用掌心壓住方向盤就好,簡直就像捏麵團似的。至於離合器與煞車,似乎是經過特別設計的,在高度上恰好是黑狗兄能搆夠得到的。
「相對於那些一醒就忘記一大半的夢,這些夢好似破碎的蛋殼,以婆娑的姿態散佈在海馬迴不同的部位。印象最深刻的,是麻糬在我面前脫下白色的襪子。」黑色箱型車SUBRU行經北投站附近的公園,六月底燥熱的天氣如同一種強酸似的分為正等待吞噬皮膚上的角質們。
「沒有冷氣嘛?」
「其實是有的。但是我認為等等要去拜訪海芋,在這之前還是暫時不要吹冷氣比較好。」黑狗兄的言語裡,似乎隱喻著一種朝聖主義的思想,而我的肌膚卻要淪為這種思想下的犧牲品。
「她悄悄地走進我房間,拉開紙門,在塌塌米上跪坐下來。像是畫漫畫時才會出現的麻糬人,如同重複曝光的影像,全身都是白色的,在月光的映射之下,呈現一種透明的乳色,臉頰則是亮得有些刺眼的程度。以麻糬而言,是相當纖細的大腿,然後他緩慢地伸出右腳,用相對粗的手指褪下襪頭,一直到腳踝的地方,然後在輕輕地將腳跟抬起,從腳趾的部分抽出襪子,接著整齊地折疊好,放在我的枕頭邊,然後靜靜的看著我睡覺。」窗外已經是林鬱蒼翠的景色,這樣說或許不恰當,因為我眼前所見似乎是一片闃黑,不過空氣中卻可以聞到綠色的香氣。
「連續好多天都是重複同樣的夢,麻糬來,會發光,跪坐下來,伸出腳,脫襪子,折好放枕邊,然後看我睡覺。但是總是只脫一只襪子,左腳的襪子像是禁咒似的,未曾在我的腦區alpha波上留下任何痕跡。」車子彎進一條小徑,我將窗戶搖下來,讓草山的空氣灌滿整部箱型車。黑狗兄則是一語不發地繼續聽我的夢,簡直像是小女孩說故事給床頭的小黑狗娃娃聽似的,若不是車子持續在行駛,我幾乎認為黑狗兄都快睡著了。
「不過昨天晚上,整個夢卻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