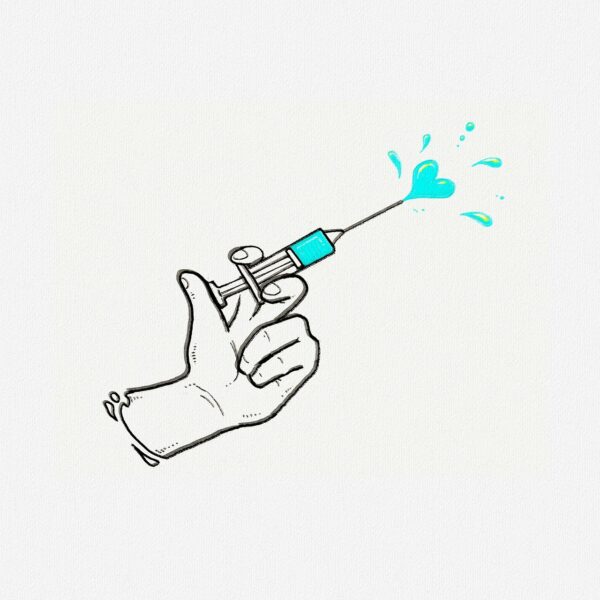「他說,要載著我走遍台灣的海岸線;他說,要挽著我的手陪我一起老;他說,我笑得時候很可愛,可愛到想把我的笑裝進玻璃瓶哩,時時溫習…」
她說著,眼淚撲簌簌地沿著鎖骨滑入V領胸口,在頸子上留下兩道隱約的淚痕。
老奶奶什麼也沒說,慈祥地給她一個擁抱。兩個相差超過1/4世紀的女人,在昏黃的燈光下相擁而泣,一旁的小妹妹歪著頭,以一種超乎年齡,很能理解的表情看著兩個女人。
這裡,是療癒食堂。
中台灣一家隱密的小鎮裡的一個小小小店,我以為只在MV裡出現,沒想到就隱匿在小村裡的一條雙樹環抱的小巷的日式平房。
黑色屋瓦上遍佈鵝黃色的落葉點點,屋子裡傳來各色香味陣陣,是香到會讓人感動想流淚那一種。
房子中央左右的部分有一張方桌,一群女孩們圍坐在一起,談著彼此的傷痛,吃著淡菜,味道卻是五味雜陳。
「我以為,我們可以一直順順地走下去…」有人很冷靜地描述她的感覺。
「為什麼?我不懂,她到底哪裡比我好?」有人很激動地問蒼天。
「上個禮拜,他還說要帶我去看星星,去好多星星的天空下數我們的夢想…」
有人想起過去的承諾如今已不再,或早已被打破,無神地凝視著筷子的尖端緩緩地說著。
「…」有的人只是嘴裡含著白飯,默默地吃著,不發一語。
一般而言,一個女孩與大家聊著情傷,最常的coping方式是--
幾個人一起罵那位男生,因為某整程度而言,這樣的方法讓受傷的一方有種「妳們懂我」的感覺。
不過這裡,卻沒有看到這樣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好像大家同在一條船上,彼此都能感受到海浪的微波盪漾,或是波濤洶湧。
一個女孩雙手握著溫熱的茶,用暖暖地蒸氣哄著形狀美好的鼻尖,茶裡面不知是否已經不小心滴入幾滴心碎的眼淚;一個女孩單手掩面,倚靠在另一女孩肩上,一隻溫暖的手輕拍她的臂膀,微微動著的嘴唇似乎是在說著「沒關係」之類的(因為隔有一點距離聽不太到);一個女孩將角落茶褐色的貓摟在懷裡,一面用臉與牠的臉磨蹭,一面閉起眼睛傾聽貓舒服的喵喵聲。
老式的電風扇一直一直捲動著幸福的滋味,在一邊轉著的同時,也把一些過去難以釋懷的傷痛一邊帶走了。
十字窗外的天空漸漸由湛藍轉為淡紫,女孩們捧著被充滿電的心,嘴裡還殘留飯菜的香氣,在天黑之前,拉起背帶結伴紛紛離開。
烘魚,蒸包,野蔬與熱茶的蒸氣,似乎還縈繞在她們身邊。
來的時候扛著心碎與傷悲,走的時候流下幸福的眼淚,這就是老奶奶開這間店的宗旨。

心理系念這麼久,愛情的文獻也讀了一年,搞到現在只知道分手的高峰期是十月(或是學期轉換時),分手會經歷五個階段,分手時最重要的療癒方式是陪伴和同理。
這些似乎都是常人都就知道的,不過就心理學的角度,這間店提供了一個相當特別的東西--無條件正向關懷。
「當我難過的時候,我還知道,這裡,有這麼一間店,無條件地為我開著,不論多晚。
當年我跟樂團的男朋友分手時,都已經是快要半夜的時間,我醉著身體從台北搭計程車一路發瘋似的到這裡,冒著大雨。老奶奶穿著花花的睡衣撐著花花的傘就出來,連圍裙都沒有圍,把我扶進角落的沙發,然後從廚房端出熱熱的紅糖薑湯,裝在白得會發出聲音似的瓷碗裡。
那時候沙發還是竹籐作的,上面連椅墊都沒有,但是我一邊拿著瓷湯匙舀著湯,卻有一種到家的感覺,眼淚不聽使喚地一直一直掉下來。」我身旁的女孩凝視著老奶奶的眼睛說著。
「那時不是妳甩他的嗎?」我望著她橙紅色的頭髮,那顏色之複雜度像極了日暮的天空。
「大家都有一個錯覺。以為甩人的人不會難過。殊不知,那只是無奈的感覺多於心痛的感覺而已。
我當時很難過,他很好,他對我也很好,只是我無法忍受他的情緒化。離開他,就像心裡被硬生生割走一塊肉似的。」
她雙手包覆著陶杯,試圖用茶葉的溫度稀釋腦海中的痛楚。
我們所坐著的籐椅(想必是當初她坐過的)對面有一隅置放著L形的沙發,也就是傳說中諮商時常見的設施之一。然而,我真正看到上面坐著人,是快天黑的時候。
一位男子穿著幾乎是全身黑色或暗色的衣服走進來,什麼話也沒有說,什麼東西也沒有點
(不過這裡幾乎是不需要點東西的,因為老奶奶似乎是依照個人需要而做的),就逕自倏地走到角落的沙發上坐下。雙手交疊於膝前,看著前方的水杯發呆。
店裡的小妹妹走過去站在他身邊,用體溫去感受他的心情。

不久,她從廚房蒸籠裡拿出帶有麵粉香氣的蒸毛巾,用小巧的手遞送給這位大哥哥。
他接過毛巾,隔著毛巾雙手深層地在眼窩上一按,幾乎是想把眼睛挖出來一般的深度。
一會兒,他將毛巾放在前方矮桌上,如同剛坐下時的姿勢,繼續看著前方,但這次的焦點是十字窗。
老奶奶好像習以為常的樣子,悄悄地端出一個盤子,上面躺著一條海苔飯捲與一杯味增湯,然後在他身邊坐下。
店內的客人就剩我與他與橙紅色頭髮的女孩,前廳的燈已經關起來了。
小妹妹一手拿著包子一邊啃食著,然後坐在藤椅旁看著老奶奶與大哥哥的方向看得出神。
男子靜靜地吃著飯捲,就像是我們都不存在一樣。
以男生的食用速度來說,他絕對算不上快,反之,像是在故意拖延什麼似地小口小口地吃。
食畢,他用舌頭將唇邊的米粒帶進嘴中,像是舔乾眼淚一樣。不過,他並沒有哭。
「第一次是她帶我來這裡的。」隔了許久,這句話突兀地不像是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樣子。
「我記得阿,那時你還小小的好Kawaii。」老奶奶用國台日混合的口音說著。
「後來,她還有再來嗎?」他問,眼神中閃爍著一點期待。
「揪故無看阿捏。」
「係發生什麼事情了?」老奶奶輕輕的皺眉,一邊拍拍他的肩。
然後又是一陣沉默。小妹妹張著嘴巴,她的世界的時間像是靜止了。
男子看了一下我們這邊,我從她的嘴角讀取到一些不信任感,於是,便拉起身旁的橙紅色頭髮的女孩一同到外面的小巷散步。
「為什麼沒有老爺爺之類的角色?」走在田埂邊,我信口問了一下橙紅色頭髮的女孩。
夜間的蟬鳴像是要諷刺一整天我們所喝的熱茶似的肆無忌憚不停地叫著。
「沒有什麼老爺爺。」她抬頭望了一下天空,像是確認星星的數目後舒了口氣說。
「那時老奶奶與她年輕時的日本情人一起在這裡開了這間食堂。
情人在光復不久後,念了一段時間台灣的大學,就決定回日本工作了。
當初也是口口聲聲地說要回來,結果還不是在日本結婚生子!」
她側著臉,踢著腳下的落葉。樹木的窸窣聲反映了夜裡的孤寂。

「講得一副好像海角七號裡的故事阿,真的假的?那小妹妹是哪裡來的阿?」
「鄰居的小孩啊。爸媽都出去外地工作了,她和老奶奶很投緣,所以假日都會來幫忙。」
她將臉轉向我這裡,然後望著我在街燈光下閃爍的銀色皮帶頭。
遠處傳來青蛙國國國地叫聲,像是不久就會要唱起寧夏的那種聲音。
夏天的夜週末的風夾帶著淺淺的溫柔,將我們兩個的腳尖捧起。巷底偶過的車燈,帶進一點現實的氛圍。
「為什麼帶我來這裡?」我終於問她。
「因為,我感覺你還沒走出來。就像那個男子一樣。」她低著頭,脈脈地說。
「走出哪裡?」我們走到一個天很寬的地方,滿天星斗,像是要把銀河都傾倒下來那樣的亮度。
「這麼多年來,你還是一樣對自己不誠實阿。」
她用鼻子輕嘆了一口氣,嘴角微微地上楊,我有時分不清這樣的表情究竟是無奈還是不耐。
我沒有回答。就像那個男子一樣。
男子這時從店裡走出來,匆匆的神色配上嚴肅得過分的皮革包,擦身而過時逸散出木槿花香水的味道。
「嘿,你知道嗎,其實,最後老爺爺有回來。」
「有回來?在哪裡?」
「在廚房外柴火間的一個小櫃子裡。每天每天,他都為每一道幸福的菜餚祈禱。」
月亮在這個時後將銀色的彎勾暈散開來,周圍的薄雲不知道是歡欣還是遺憾地將天空渡讓給它,臨走前身上沾滿粼粼銀光。
然後她作勢請我別出聲,因為灌木叢間也出現了一點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