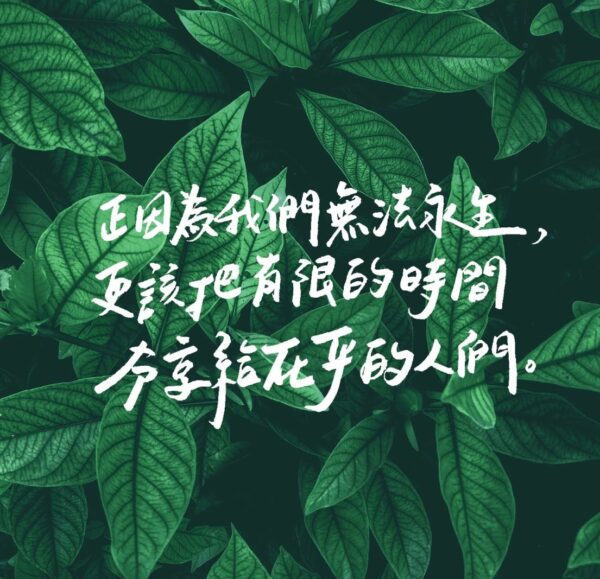「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在一點一點地死去噢。」濛濛說,好像在闡述某一種天啟似的。我們在台北車站的大廳,揀了黑色的一格在上面躺了下來。望著天花板,似乎在等一種聲音降臨。但其實什麼也沒有降臨。
「這樣講也未免太悲哀了吧?」我說,然後把從伊東屋買來的拉拉熊布偶放在肚臍上,用身體的一部分共享它的慵懶。
「正好相反!正因為每天你都在死去一點,你不覺得把剩下的人生,認真的好好過下去才更為重要嗎?」
「像這樣躺在地上,等待外星人或預言出現之類的,認真地活下去嗎?」我把拉拉熊布偶從我的肚皮上面拿下來,讓牠躺在我右邊。牠兩只無神的眼睛望著挑高天花板,好像在說「哎呀,時間就算這樣一點一點地浪費下去也沒關係的喏!」
「嘿,小花君。你覺得,如果有生命的神存在的話,會是什麼樣子的?」她問我,繼續盯著上方看著。
「我也不知道耶。可能像狸貓那樣會抱著餅乾,一點一點地啃著,然後撥開雲從天堂看著我們繼續談論著生命、談論著死亡、談論著明天吧?」
「為什麼是狸貓呢?為什麼不是無尾熊或是企鵝之類的呢?」

「不知道,總覺得不能是其他的動物。想像的概念化啊!狸貓或許是一個恰到好處的神。無尾熊也可以,企鵝也罷,但總覺得狸貓卡滋卡滋地吃著仙貝,一直吃下去比較好的樣子。」
「那企鵝和無尾熊怎麼辦?他們也很可愛啊!這樣他們會寂寞呢……」
「這世界不是靠可愛和可憐就可以過活的噢。這可是活生生的現實阿!什麼生命的神也好、地下水道的神也好,不是隨隨便就可以當的阿。那些權力、支配、既得利益者是固定的喔,總是要有某種程度的邪惡和歪斜才能勝任的。」
「正因為我們的社會太不勇敢了,所以才會被不勇敢的人所支配著?」
「是阿,然後一邊看著那些呼喚著勇氣與堅強的電影、卡通、語錄什麼的,藉此讓自己心裡面舒服一點。然後跟自己說:嘿!我和你們那些懦弱的傢伙可不一樣噢!我心裡面有一塊正堅強而勇敢地活著呢!」我一邊表演一邊說,但她似乎不怎麼熱心聽的樣子。
「嘿,無尾熊真的不行嗎?我說生命的神之類的。」濛濛把頭轉過來對我說,側邊馬尾飄過來小麥的香味,讓我想到小王子金黃色的頭髮。
「戴、戴上粗框眼鏡的話,或許可以嘗試當看看地下水道的神吧?」我說,特地把目光鎖定在天花板上的一點。
濛濛一下子靠得太近,讓我的脖子瞬間變得僵硬。
「地下水道啊……應該也是很孤單的吧。可憐的粗框無尾熊地下水道神……為什麼生命的神就不可以,地下水道就沒問題呢?」濛濛一臉哀怨又複合著一點憐惜的樣子。其實我一點也不懂,這樣沒有意義的話題為什麼可以持續這麼久。
「嘿,小花君,你覺得,地下水道的神,有一天能改變世界嗎?」要命,果然是沒完沒了啊!
「可能很難吧。畢竟只是一隻戴粗框眼鏡的熊阿,偶而擦擦眼鏡、偶爾吃吃庫存的尤加利葉什麼的。夢想啦、改變啦,即使是地下水道的神,也很難撼動這世界的吧?」

「你知道嗎,你有奇怪的地方噢。這裡大概壞掉了。」說著用食指戳了我的前額頭。有點痛。
「你說腦袋有洞嗎?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啊,只是不相信那些無法實現的事情罷了。」我說,揉一揉右前額剛剛被濛濛戳的地方。
車站裡的人漸漸散去,店家也一間一間關起。我甚至想,如果世界上有一個沒有現實的地方,或許粗框眼鏡的無尾熊就可以好好地、安穩地在那裡,當生命的神。
「我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生命,可是到頭來,你會發現還有更多邪惡的人、黑乎乎的東西在主宰著你。」我說,一邊想像著無尾熊帶著王冠手持權杖坐在椅子上,在那裏當神的樣子。
「為什麼我們的世界要如此黑乎乎不可呢?如果每天我們都會比前一天多死去一點點,為什麼不能互相關愛、彼此擁抱呢?」
「因為每個人都害怕死亡吧,那些邪惡、黑乎乎的東西也怕。」我說。
廣場上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我盡量地想著,狸貓抱著餅乾,在宇宙的角落,一邊吃,一邊凝視著我們生命的模樣。
但不知為什麼,無論如何都無法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