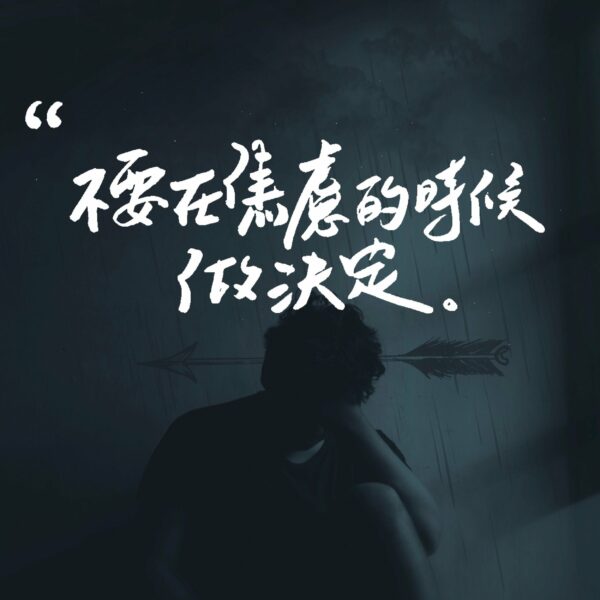「那麼,那邊好玩嗎?」我說,然後漫不經心地一直看著櫃台。
「風景很美,小孩很多,心情也很多。」
「心情?」我擺出一貫不解的眼神。
感覺我應該點花生巧克力醬冰沙,然後她點Double Mocha 之類的。
只是這麼冷的天氣,我實在沒有像她一樣喝冰沙的勇氣。
「是阿,與其說是為了他走這一趟,倒不如說,是為了自己。」
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她聊她的事情,一邊端詳著她全身俐落又優雅的OL打扮,腦袋裡偷偷想像著程又青。
帥氣滿分的服務生把Double Mocha放在我桌上,說完請慢用之後,她身邊所圍繞的時間似乎就開始不受我的管控。
「我想我無法放下的,不是他本身,而是零四年夏天他從陽光盛開的加州寄來的那張長滿香蕉和芒果樹的卡片。」
她一邊說著說著,將目光投向前方車水馬龍的基隆路,眼神像是要望穿那片落地玻璃卻又留有一點捨不得,最後想想終於作罷的那種樣子。
然後,她從大紅色的皮製包包裡拿出一張小名信片,比我想像的還要大張。
我試著翻轉看看,封面是一棵大的嚇死人的樹,背面用Cerulean Blue的墨水密密麻麻地寫了一串字……
──「我好想妳,好想好想。站在 Coronodo Island,我覺得自己好像被海浪捲動著的貝殼,被思念的浪花濤弄得心裡癢癢的。 如果我真的是那只貝殼,我想我會寂寞地落淚噢。 可是我想,妳也在一方默默地等待著,就忍著沒有哭。 這裡的海很美,日落的時候,鯨魚或海豚都會在海面上跳舞祝賀。 往墨西哥的方向有一條像絲帶一樣很長的橋,好像一路可以延伸到太平洋另一邊的那一種。 我們畢業之後,我一定要帶妳再來玩一次,就算是在沙灘上打滾,撿貝殼也好。」–Brad

因為工作的關係需要找一件套裝的配件,翻箱倒篋地把骨董櫥櫃都找了一遍,無意間在櫃子深處,我曾經很喜歡的那件海藍色洋裝袖子夾層內,掉出了這張明信片。雖然字跡已經有點模糊,當時的浪漫卻仍如故。
我舒了一口氣,盯著這張卡片端詳了不知道有多久。
為了確認並彌封這段不慎被掀開的過去,我排了長假,隻身來到 Coronodo Island
從觀光遊覽車揹著大帆布包下來,左腳和島接觸的那一剎那,心中並沒預期的那種撼動,可是頭頂上的陽光似乎微微地削減了一些。
我試圖找尋他所說的那片有鯨魚跳舞的海岸,但是遍尋週遭店家,他們都以為我在開玩笑。
經過一天的折騰,我決定站在一個可以眺望Coronado Island bridge的地方,閉上眼睛,想像那年曾經很思念我的他。
卻遺憾地發現,我幾乎快想不起他的臉了。
當年是多麼的渴望能忘記他的長相、忘記他承諾我那段浪漫又不切實際的話語、忘記和他相處的那些美麗記憶,卻總是無法擺脫,日日夜夜被悲傷侵襲;如今真的忘記了,反而有點惆悵和惋惜。
在沙灘上我佇立許久,海浪若無其事又帶點藍調風情地帶來沙沙的聲音,試著彎腰去尋貝殼,卻不見任何貝殼的蹤跡。沙灘管理員用非常難懂的墨西哥腔英語跟我說,這裡因為是觀光景點,每天都有人定時清理沙灘上的貝殼避免扎傷。
我抱持著不知道是漠然還是失望的心情,準備徒步走回預定好的旅店。
當我正要轉身的時候,發現沙灘上有一個扇形貝殼的痕跡。
那深度和紋理,好像就要刻進我心裡一樣。
可是不出幾秒鐘的時間,潮水就湧來,注入,然後將貝殼的最後一點痕跡也一起帶走。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我感覺心裡生起一種暖意,一些多年來一直隱隱作痛,殘缺淌血的什麼,似乎被弭平、被治癒了。」

她說完之後,舒了一口氣,稍稍停止了一下。將視線拉近到桌上那杯冰淇淋已經融化一半的花生巧克力醬冰沙上。
「再不喝的話,要變成巧克力歐蕾了喔!」我說。
「那也不錯阿。什麼東西都會改變的,至少它曾經是花生巧克力醬冰沙。」
「其實當年你怎麼沒拿書卷獎畢業呢?哲學系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啊!」
然後,我們都笑了。
在嬉笑之間,我好像開始看見,七年前,這片海灘上面曾經有一位十九歲的男孩,瞇著眼睛看著海, 抿著嘴忍住淚水,想念著海另一端的女孩,那種可愛的模樣。
看樣子,感情固然讓人痛讓人哭讓人無助,但也讓我們學會珍惜擁有,接受失去。
試著想有一天,當妳白髮蒼蒼,再回頭看看這些從前,究竟是會哭著抱怨,還是會用微笑的嘴角,拍拍當年的自己的肩?
[1]圖片若有侵權,歡迎留言或來信告知,立即移除,謝謝。
[2]謝謝告訴我這段甜美的好姊妹(唉我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角色),還有被我們佔據一下午的5 Senses Caf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