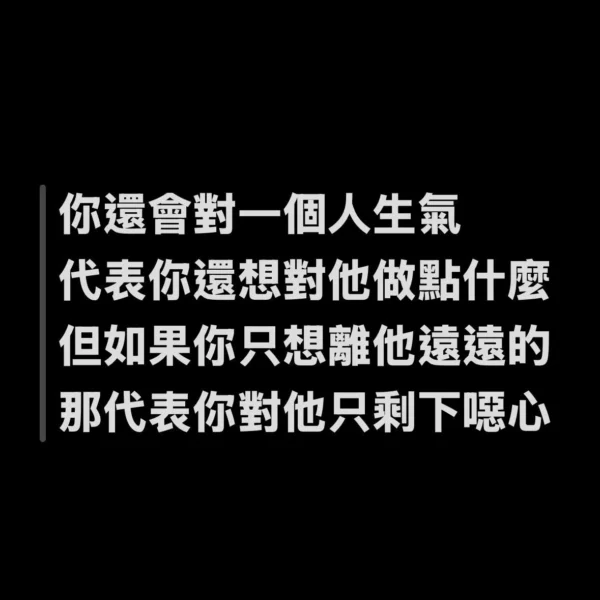“你手上那是什麼?”我看了心理師叮噹貓抱了一堆濕濕黏黏滑滑的紙從晤談室走出來。
“剛剛那位個案的憤怒阿。”他稀鬆平常地說著,語氣像是問今天中午去哪裡吃一樣。
“憤怒?”我重複他的句末一次。
在這裡,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沒有很認真聽別人說話,卻又想回應他,不讓它感覺到被敷衍的話,最有效的方法是重複句末詞+尾音上揚。
這樣,他就會重新把事情講得更清楚一些了。這個方法,能在你精神耗弱又希望了解事件的時候,對彼此都能幫上很大的忙。
(不過我這裡可是很認真在聽的,因為,叮噹貓完全吸引了我的興趣。)
“是阿,我請他在紙上畫出他的憤怒。他畫完之後,就叫我幫他拿著,然後一邊踹阿踢的,就變成這副模樣了。”
我看著皺成一團的紙上貼了皺成一團的紙,嘴巴驚訝地闔不起來。
“那為什麼會有膠水呢?”我問。
“喔。我請他在另外一張紙上重組。”
“然後他在上面擠了一坨一坨的膠水。把他的憤怒都貼上去。”
我今天才發現,原來憤怒也是有形狀的。
我們對別人、對壓力、對自己甚至有時候對不知名的對象生氣,最終撕裂了情緒、零亂了自己。
如果站在這碎了一地的情緒裡面,我們還能看見自己的樣子嗎?還能用什麼方法重組這些情緒嗎?
或者,更進一步的說–如果撕去了情緒以後,我們還剩下些什麼?
月底月初,又是忙碌慌亂的季節交替。
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喪失了意義感,心想我在這個時空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怎麼也想不通,就只好到山邊走走,看看花木草樹,落英繽紛。
然後我發現,前些天跑步時還看見滿載花簇的櫻花樹,而今已成一片光禿。
而那些原先光禿的桃、杏、李、鳳凰,像是彼此說好似的,交替地開著、謝著。

“生了病以後,每天像坐雲霄飛車。我好像,已經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樣子了。”幫忙做測驗的時候,一位個案說。
其實,他是不會消失的。
我們的情緒就像這些開落的花,不論季節如何更迭,行人多麼匆匆,風雲幾次來去,日月怎樣遞移,開花的樹或許不再開花,凋零一地的樹也可能在某幾些枝頭發起新芽,可是,這棵樹始終在。那。裏。
就像真實的我們的自己,不會因為身邊的人來來去去,而有所挪移。
有人說,最終能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
但我覺得,真正陪伴自己的是那些開謝的花蕊,還有身邊看著我們送走時間的人們。
就像每天中午,趴在欄杆邊,等待我跑完回到醫院的那隻小狗兒一樣。
p.s.1為確保隱私,涉及個案的內容經大幅修改與模糊化。
p.s.2終於有一篇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得了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