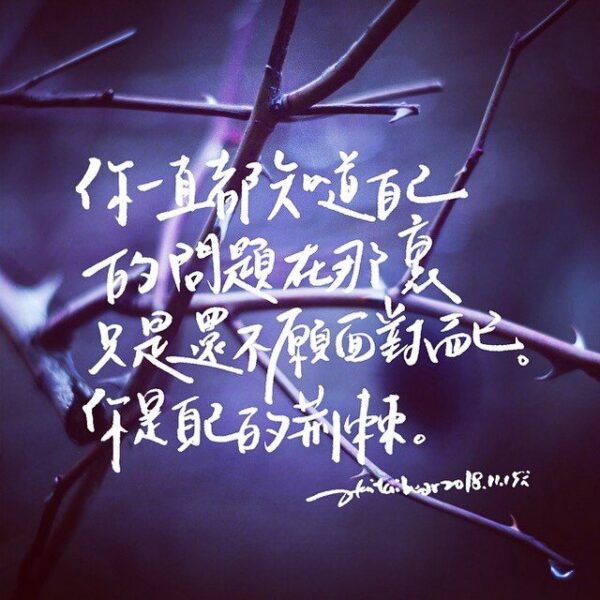我對海邊與跑步有一種期待。

那種期待就像是歲月拖著長長的尾巴在沙灘上劃出髮流般的弧線,輕輕地騷動著背脊上微微隆起的骨骼,癢進心裡。

那種期待以一種淡紫色膠底跑鞋親吻柏油路面的姿態,機機嘎嘎地訴說著水泡夾雜著鹽分燥熱的黏膩感,滲進足底。

那種期待正瞇著眼隱約浮現紮起馬尾的中法混血兒陽陽的臍帶,一邊連結著負載衝突與矛盾的胎盤,一邊和自我超越與逃避的肚臍接壤。

透過這條臍帶所餵哺的期待,源源不絕地將社會的眼光傳遞到陽陽兩片杏頁般大腦的中央溝,用一種強烈的不和諧感隔閡著左右腦。

看著長鏡頭下的陽陽的髮際,不禁讓我想起法國Le Havre港口的海岸線,從城市的河岸一直延伸出去的那種寂寞;她雖不是一個人在台灣,卻是以一個人的勇氣活著,跑著,呼吸著,甚至喘息著。
「在下雨天的Le Havre港口,從橋上望著穿越市中心的河往海的那一邊沁入,灰灰的雨和灰灰的大樓醞釀著沉重的河水與海水交融混合,心裡的一些什麼也跟著起了變化。」這是我整理了數天,才能以較明確的文字描述我看完陽陽的感覺。
走出戲院,我有長久一段時間無法說話,寂靜的空氣像是劇中長長的鏡,連呼吸都顯得奢侈。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是由應然我(妳是混血兒應該會說法語吧?念心理系應該可以看透人心吧?)構築的世界,還是由理想我(我想跑,我想飛,我想自我超越)所拚湊的世界?或者,我們註定如Le Havre港口的河水一般,拉扯著淡與鹹,掙扎於應然與理想之間?
「人被槍擊中的話,是會流血的噢。」我想起<人造衛星期情人>裡小堇說的話。
「人被槍擊中的話,是會流血的噢。」我試著將這句話說出嘴巴,很遺憾的並沒有魔法,心裡面那些濃稠的什麼似乎還是沒有散去。

女孩的成長是一連串調合自己與他人期待的複雜歷程,唯有像吃西瓜一樣從正中央剖開,才能面對兩瓣炙熱果肉中參雜的黑色斑點;而男孩的成長是常常故意忘記西瓜的存在,或把西瓜藏起來的歷程。
—
「嘿,西瓜在這裡吶!」在東區新光三越徒步區發現西瓜的熊耳兔說。
「哪裡有西瓜?」我說。
四周往來的行人像是被按了靜音與慢動作鍵的彩色電視,我的視野如同河底的蜉蝣,穿梭在人所堆積的河泥,櫥窗裡流行服飾的殘影包圍著我的心,湧起一種難過像剛下的雨。

於是,熊耳兔正式地在七月炎熱的信義區磚道上離開我,路的盡頭是前年夏天的秘密海、天空藍,與摩斯的海苔飯糰。
附上品冠播放器,誰想跟我去聽演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