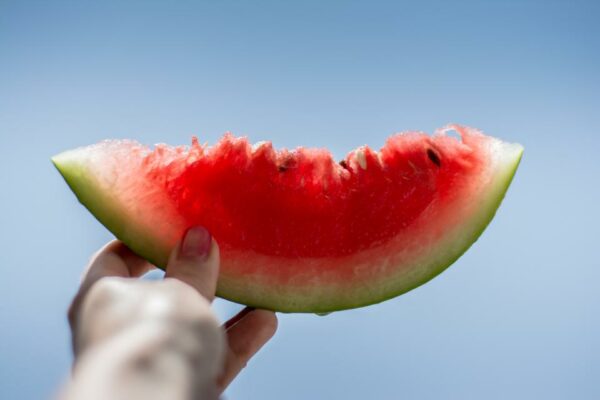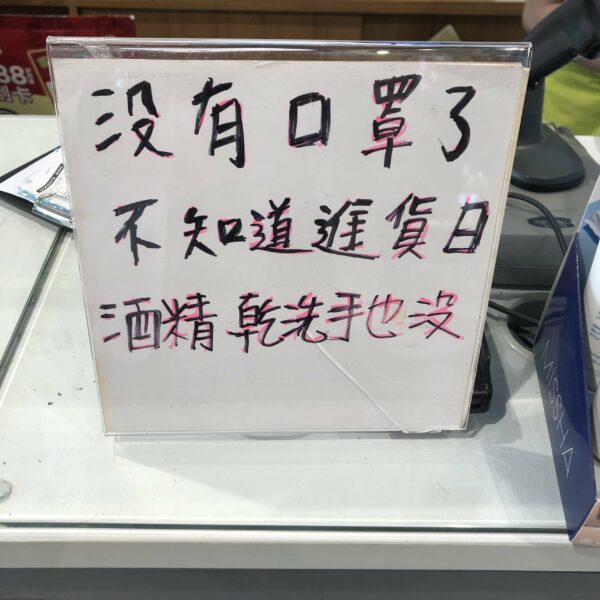“大寶,二寶。爸爸買了兩隻雞腿,放在冰箱裡面。明天中午記得拿出來吃喔!”
他用模糊又勉強才能辨識出來的聲音在我後面叮嚀著。每次放假我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別說是吃飯了,如果能有空喝口咖啡就已經是萬幸。
可是,每週每週,他卻像是永不停歇的小蜜蜂般,在我身邊繞來繞去,叮嚀東叮嚀西。
我數度都覺得很煩,在裡面已經被管得體無完膚了,難得回家卻連一點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好像把連長隊長輔導長一起打包回家一樣。
“大寶,吃飽了沒?”
“大寶,洗完澡窗戶要開,要把衣服帶進浴室才不會刮丟(台)。”
“大寶,早點回家,爸爸等你噢。”
“大寶,你這樣穿不夠,再去多穿一件。雨衣帶了沒?錢包帶了沒?手機呢?”
“已經四點了喔,你這樣會來不及,趕快出門,別東摸西摸!”
“哎呀,不要在書包旁邊掛東掛西的啦,不好看。你已經長大了。”
“大寶,你好久沒有在家吃晚餐了。回來陪媽媽好不好。”
“大寶,這個下次不要買了,不好吃,爸爸也吃不完。不要亂花錢。”
儘管我已經穿了五件之多他還嫌不夠,每次都說下次不再提醒我了,卻每次又食言;
明明是自己需要人陪,還把責任推給我媽;
常常一邊這樣說,一邊每次都津津有味地吃完那些包子饅頭波羅油,麵包油條海鮮粥。
當然,覺得更煩的是我弟。
因為我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要我回家,就等著挨罵,從髒亂的床鋪到不愛吃飯都是被念的開頭,
所以,老哥回家=安寧結束+災難開始,
他又得清晨六點時蓋著棉被迅速臥倒,忍受我被轟炸的大小聲,
凌晨三點時巴望著我能早點關電腦不要等到老爸催我去睡,因為這樣他又不用睡了。
他很無奈,無奈得是有一個始終長不大的不可靠老哥
我也很無奈,無奈我總是給身邊關懷我的人帶來無止盡的無奈
從小他就比較像哥哥,打球運動修機車,我反而幼稚得像弟弟,只會讀書畫圖玩遊戲
很可能,這些一開始早就註定好了吧,哀。

每次放假,當鄰兵都把衣服綁上名條丟進洗衣籃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將一週的髒衣服塞到由懶熊中隊所戒備的黃埔大背包裡,
然後重重地背回家,又重重地背回營。
“你怎麼不給洗衣部的阿姨洗?不是交很多錢?”鄰兵問我。
“嗯,因為我爸把洗衣服當作事他的志業,如果沒有洗到衣服的話,他會很沮喪。”我說
於是,每週每週,我跟我弟的兩大堆衣服便成為他Dopamine的來源。
我踏進家門,一件一件地把衣服丟出來的時候,他感動的眼神只差沒有把嘴上的顫抖地菸掉在地上。
是的,他還抽菸。
即使是在中風多次又癌症侵襲如風中殘燭的今天,他還是抽菸。
“你再抽菸的話,出院以後我就不跟你說話了。”我弟在他上一次中風,傷及Broca area的時候嚴厲地跟他說。
那時的阿爸連我們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一臉感到無力就快哭泣的樣子,只好頻頻點頭答應。
可是,承諾似乎是世界上最不值得相信的東西。
就像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幾乎所有車禍斷腿的人都會在一年內回覆正常的人生
就像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八成為分手難過心碎發誓不再愛的人都會在六個月後重拾並相信愛的可能
阿爸的抽菸也在手術後的第四個年頭,從偷偷摸摸變得光明正大,
而我弟,也變得除了必要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不跟他說一句話。

其實我並不怪他,就像我也改不掉咬指甲的壞習慣,
畢竟每個人都有一些無法戒掉的痼癖,打靶時才會被班長訐譙到飛上天去
多吸一包菸或許少活幾分幾年,但這分分年年在無限的宇宙裡卻只是渺渺一粟。
如果抽起菸來能讓他忘卻寂寞,燃燒肺泡麻醉失落何嘗不是一種方法?
“或許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我爸是健康的。”從大二就知道平行時空假說的我每次都這樣想。
朋友都說我太過豁然,我笑他們看不穿。
可是,真正看不穿的是我。
所有的寂寞都不是缺乏關注,而是得不到想要的關注。
而寂寞的人最常對抗寂寞的方式,是附出關心,給予他所重視的那些人。
希望能透過這樣的關懷,這樣的脆弱,這樣的在乎
換得對方一點點的回應,一些些的關注。
—-甚至,只要輕輕點頭,接受他給的那些好,就可以了。
“我不想吃雞腿。”我說。
是阿,我卻殘忍得連這樣簡單的心,都沒有回應他。
調到新的單位以後菜色很好,但一切都變得匆忙又難以適應,連每餐吃飯都只有7分鐘,無福消受的情形下,
早就習慣把雞翅雞腿給別人,隨意扒兩口麵就下餐廳的日子。
反正,有零食與懶熊陪我度日。
況且,那兩隻雞腿還要花時間烹飪,我寧可拿這些時間去解放我的腸胃(嗯,我說得很含蓄)。
“不行,要吃才會有營養。一支給你,一支給弟弟”阿爸側著身,一手抓著我房間的門把說。
“你拿去吃,我不吃。”我說,都幾歲了拜託。
有好幾分鐘的時間,都沒有聽見他的回應。
不過我想這樣正好,他可能放棄了,我連心戰喊話都不用。
“爸爸也想吃,可是爸爸沒辦法吞啦…”聽他再度含糊地說這句的時候,心裡微微地震了一下。
在我風花雪月幾十載,唱歌答數幾十天的日子裡,
那個曾經像龍貓一樣大口吃飯大口喝湯的阿爸,
曾經壯到把牛排館椅子坐壞的阿爸,
臉頰已經開始凹陷,頭髮稀疏地蒼白著,連爬樓梯都變得緩慢了起來,
如今,卻連最愛嗑的雞腿,都咬不動。

發展心理學家一致地指出,孩子是父母身體健康與未竟理想的延伸。
如今就連一支簡單的雞腿,我都輕易地回絕,我真得是可惡的有春(台)。
當我正考慮要不要乾脆一口答應他避免麻煩時,阿爸又把我房間的窗戶打開,和緩地跟我說:
“大寶,如果你不喜歡吃沒關係放著好了。以前爸爸當兵,你阿公在我放假的時候,都會煮雞腿給我吃,那時我雖然在總統府前面站到腳痠快受不了,一想到家裡的雞腿,就會忍著眼淚繼續撐下去。結果弟弟剛剛說你們每天都有肉可以吃,對不起,爸爸不知道現在雞腿退流行了。”
他用含著滷蛋的方式說完以後,把窗戶關默默地起來,坐回他客廳的龍椅上盯著電視繼續發呆。
退。流。行?我幾乎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一股強大的罪惡感無懈可及地襲來,How can I…
若不是阿爸房間他桌上那張比國軍公仔還帥氣挺拔的黑白照片,我幾乎不記得他當過憲兵,站過府前。
而今別說拿槍了,連拿菸都會抖。看著他被電視看著的呆滯眼神,有一種說不出的心酸難過。
我突然想起阿罵跟我說的話:
“哩阿公彼個時陣,工作到很晚回來,我都卡兩個蛋,炒個青菜淋上一點肉醬,給他當消夜。安捏就算補了耶,你哉嗯哉!”
到阿爸房間穿換褲子準備出門的時候,我看見阿公那張黑白的軍裝照,突然覺得一家子三代帥氣似乎是可以遺傳的(自己說~)。
只是隨著生活變得容易,我們卻變得更為討債(台)不懂珍惜。
一腳套進褲子,突然覺得有點對不起列祖列宗,把自己的身體搞得跟骷髏一樣。
想到照片裡十六歲就歷經東征,北發,剿匪,抗戰,大陸淪陷等等的那個少年;
想到旁邊那個戴著白色安全帽雄赳赳氣昂昂的十八歲青年,騎著白色重機車載著也曾經年輕的阿母在新公園附近兜圈,
再看看自己越穿越小的褲管與背包上的花俏裝備,不禁擔心這雄壯的傳承,會不會因為我變得熊狀起來。
“雖然你可能很討厭你爸,覺得他很煩,可是如果不是他,你連覺得煩的機會都沒有。
而且,在過一段時間你就會發現,所謂的由男孩變成男人,不過就是變得更像你爸的過程。”
某一個前女友曾這樣告誡我,並勸我好好孝順家人,儘管她自己的家已經分崩離析。
1939年背著彈藥在叢林裡追趕日軍的阿公
1978年扛著步槍在凱道前等待阿母的阿爸,以及
2012年率領拉拉熊在網路上終結孤單的我
在不同的時代守候不同的夢,在同樣的青春驅逐同樣的寂寞
或許,夢想會跟著歲月斑白
或許,青春會隨著長大殞落
也或許,年紀的隔閡,會使不同時代的我們變得不知道該如何打開心防
可是,看著這兩張照片,我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之前,連長都說軍旅生活是男人之間的共享記憶我都以為他在屁,
而今,我卻發現這些記憶不只是共享而已。
而是一種連繫。
“大寶,你要去哪裡?”我出門的時候,阿爸問我。
“去超市買醬油跟辣椒。”說著我就拿起機車鑰匙。
“買辣椒做什麼?”他問。
“做左宗棠雞阿,你不是說你咬不動。”
“甚麼唐雞?”他說,可是我已經轉身下樓,故作帥氣。
就算我們的心還有很大一段的距離,
就算他還是覺得我太幼稚還在叛逆
就算我還是覺得他很煩很吵很機車,
就當作算在我們曾經都拿過步槍的份上,從這一刻起,循著這連繫找到共同的準星。

回家之後,阿爸不知為何很早就進房睡了。
在他半夜起床晾衣服前,我躡手躡腳,偷偷地把成功嶺那張光頭彩色照片塞到他桌墊底下,
雖然和另外兩張黑白的擺在一起有一點不搭,可是總算是勉強可以切齊班面。
突然,一個人拍了拍我的右肩膀。
“哥,把我這張也放進去吧。”說著把他在屏東結訓的照片給我。
這是我頭一次覺得,老弟的迷彩服上傘徽沒那麼刺眼。
也是我頭一次發現,幼稚與成熟的界限,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明顯。
四張大小不一的照片擺在一起,
好像因此完整了心裡的一些什麼似的。